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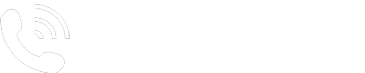
愿白鹿长驻此原 陈忠实
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
这是白居易一首七绝中的两句。每有机缘上原,心头便会涌出这首绝句,情绪顿时也会畅朗起来。我无法想象千余年前的白居易纵马白鹿原上寻到的是怎样一幅秋色美景,单是眼前的一派绿色,已经让我沉醉了。
一条新修的宽敞的公路盘旋在西边原坡上,两边是层层叠叠的绿树。刚刚从酷暑进入初秋,尽管杨树柳树槐树等树木的树冠呈现着深色和浅色的小小差异,却依然流露着蓬勃的气象。草木清爽的气味,诱使我连续深呼吸。这里曾经是荒坡和梯田。荒坡上长满枣刺和杂草。梯田里一年只种一料麦子,因为缺水缺肥,麦子长得矮小细瘦如同猴子的黄毛,收割时搭不住镰刀,只能用手薅,民间戏称薅猴毛,产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大约不过10年前,那种延续了不知多少年的广种薄收乃至无收的景象中止了,退耕还林,便有了这一派让上原和下原的人心旷神怡的绿色。
上原的路大约走到一半,有一道平台,自南到北散落着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俗称二道原。民办大学思源学院已成气候,随坡倚势建造成一幢幢楼房,校园里如同精心构设的花园,四季轮番开放的花草和花树,弥漫着种种诱人的香气。这里活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余名学子,避开了都市的喧嚣,在这一方天地汲取知识。校方扶持建立了白鹿书院,我常和一些文学朋友到书院交流,尽管他们多是走南闯北见惯了奇山异水的人,也多感佩这一方地域独有的脉象。大约10年前,这所大学的创始人
绿树掩映着的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既是古老的,又是新生的,古老到和这道原的历史一样悠久,新生在于现在的村庄已经完全改换出一派新的风貌,一幢幢二层小楼或平房,从绿树的空隙间显露出来。如果走进村巷,便会看到甚为讲究的一个个农家院的门楼上都有题款。几乎看不到土坯垒墙的传承了千年的厦房了。沟通每一个村庄的道路全部实现了硬化——水泥路面,永久性地告别了泥泞小路。我曾陪《白鹿原》剧组的朋友踏访原上村庄寻找外景地,失望而归,上世纪的白鹿村的影像荡然无存。我不为剧组的失望而失望,倒为原上的乡党而庆幸,他们终于获得了安逸富足的生活,既不为锅里缺米缺面而熬煎,也不为屋漏而愁肠百结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每触及一景,便牵出这一景地昨天的景象来。似乎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一种自然的不可违逆的心理反应,昨天的贫瘠景象铸存太久,而今天焕然一新的景象来得太快,作为这道原的亲历者,发生今天与昨天的鲜明而又强烈的对比,欣然的感触和感慨就是本能的心理反应了。
因为一只白鹿的出现,这道原便有了象征着吉祥安泰的白鹿的名称。随后,汉文帝葬在白鹿原西北的原坡上,原坡根下流淌着灞水,文史典籍称为灞陵,这道原也被改名为灞陵原,民间却少有人说。自北宋大将军狄青在原上屯兵驯马,这道原又被改换为狄寨原,一直沿用至今,白鹿原的名字早已淹没以至消亡了。近年间,因为拙作《白鹿原》的发行,这个富于诗意也象征着吉祥安泰的白鹿原的名字又复活了。白鹿原名称的重新复归,恰当其时,多少代人期盼向往的富裕和平的日子已经实现,却是改革开放的科学而又务实的富民国策实施的结果。
愿白鹿长驻此原。